问起“疫情哪天开始封城”,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搜索那个官方日期——2020年1月23日,武汉,这个日期已被刻入历史,成为集体记忆的坐标,当我们真正回溯那段时光,会发现每个人的“封城第一天”其实各不相同,对有些人而言,封城始于超市里突然空荡的货架;对另一些人,是手机弹出的紧急通知;还有人记忆中的起点,是那张迟迟未能兑现的返乡车票,官方日期勾勒了历史的轮廓,而千万个私人记忆的碎片,才拼凑出那个冬天真实的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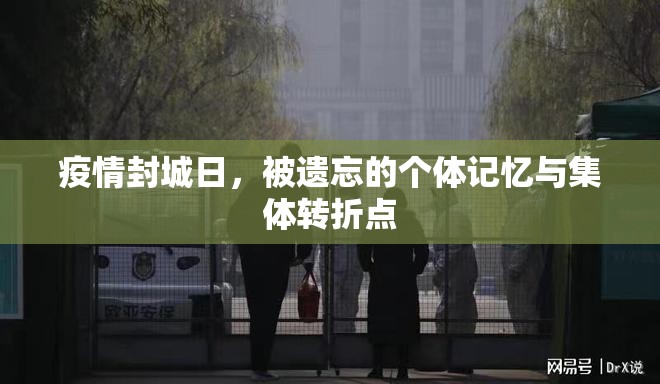
历史书写的本质,往往是将复杂事件简化为清晰的时间节点,2020年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发布封城通告,这个时刻被载入史册,成为全球抗疫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精确到分秒的记录,满足了人类对秩序和确定性的渴望,这种宏观叙事之下,掩盖了无数个体时间线的交错与断裂,一个在22日晚侥幸离开武汉的人,他的“封城日”是提前的;而医院里连续加班多日的医护人员,感觉封城早已在病床告急时就开始,时间在这里呈现出奇特的相对性——公共时间的统一刻度,与私人体验的千差万别并存。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张力,在封城这一事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共享同一个历史事件,却拥有截然不同的记忆版本,社会学学者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理论,指出记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疫情三年后的今天,当人们谈论“封城开始时”,更多指向的是那个官方日期,而非个人体验,这种记忆的标准化过程,某种程度上是创伤后应激的反应——社会需要统一的叙事来愈合伤口,个体则通过融入集体记忆来获得安全感。
丢失个体视角的疫情史是不完整的,那位在封城前夜驱车十二小时将口罩运抵武汉的司机,他的“封城日”充满使命感的炽热;那位因封城滞留武汉78天的外地游客,他的记忆则饱含无助与焦虑,这些细微的个人史,共同构成了疫情的全貌,正如历史学家王明珂所言,历史不是单数,而是复数的“ histories”。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疫情封城不仅是公共卫生事件,更是社会关系的显影剂,封城那一刻起,我们习以为常的流动自由被暂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重新定义,亲戚间的团圆饭、朋友间的咖啡馆小聚、同事间的面对面交流——这些构成日常生活的碎片,突然变得珍贵而遥远,封城在物理上隔离了人群,却在情感上让许多人更紧密地联结,社区微信群里的互助信息、阳台上的集体合唱、对医护人员的自发致敬,这些行为重新编织了社会的纽带。
疫情封城日,因而成为一个多重意义的时间标记,它既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起点,也是社会价值观的检验时刻;既是个人生活的转折点,也是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契机,当我们今天回顾“疫情哪天开始封城”,不应仅满足于检索那个标准答案,而应尝试复原那些被宏观叙事淹没的个体声音。
在未来的历史书写中,或许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精确到分秒的官方时间表,更应有那些普通人的时间刻度——那位最后一次乘坐地铁通勤的上班族,那位在封城前举办最后一场婚礼的新人,那位在小区封闭前还能自由散步的老人,他们的“封城第一天”,共同构成了这场世纪疫情的完整图景。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但记忆属于每一个亲历者,疫情终将过去,而封城那一天所引发关于自由与安全、个人与集体、生命与经济的思考,将持续回荡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当我们追问“疫情哪天开始封城”,我们真正寻找的,或许是自己在那段特殊岁月里的位置与意义。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