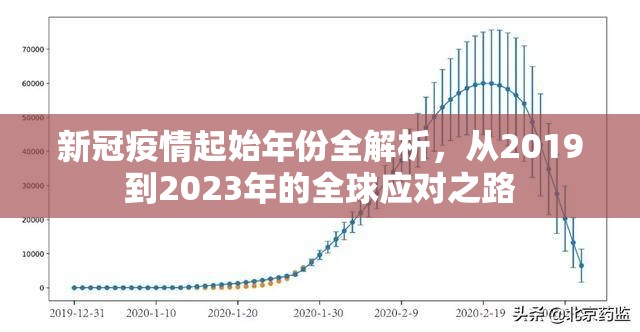当口罩成为日常配饰,当核酸检测化作生活routine,当“隔离”与“密接”成为通用词汇,一个萦绕在每个人心头的问题愈发清晰:新冠疫情,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答案却如同一团迷雾,交织着科学、社会与政治的复杂经纬,它没有一个简单的日期可以标注,其“结束”并非戛然而止,而更可能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渡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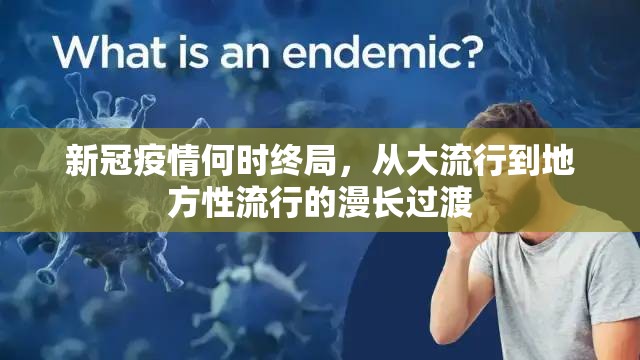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界定何为“结束”,是病毒彻底从地球消失,如天花般被根除?从新冠病毒(SARS-CoV-2)的特性看,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广泛的动物宿主、强大的变异能力及无症状传播特性,决定了它将与人类长期共存,更现实的“结束”标志,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全球大流行”(Pandemic)状态终结,疫情转变为“地方性流行”(Endemic),这意味着病毒仍在特定区域持续存在,但传播水平可控,对医疗系统的冲击降至可承受范围,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人们学会与之共存。
达到这一状态的路径何在?核心在于构建稳固的全球免疫屏障,这有赖于两大支柱:高水平的疫苗接种与自然感染获得的免疫,现实挑战巨大,全球疫苗分配严重不均,欠发达国家接种率低迷,为病毒变异提供了温床,奥密克戎(Omicron)及其亚变种的出现便是明证,疫苗免疫力会随时间衰减,针对新变种的特异性疫苗研发仍在追赶,新冠病毒的变异方向存在不确定性,未来是否会涌现出兼具高传染性、高致病性与强免疫逃逸能力的“超级变种”,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些科学上的未知数,直接拉长了疫情终结的时间表。
疫情的“结束”并非纯粹的医学命题,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建构过程,当社会集体心态从“恐慌”转向“疲惫”,再从“疲惫”过渡到“接纳”,疫情的“社会性终结”或许会早于其“医学性终结”,公众对防疫措施的依从性、对风险的感知与耐受度,以及媒体叙事的方向,都将共同塑造“结束”的节点,若民众普遍认为病毒威胁已降至与流感相当,即使医学专家持保留意见,社会生活的正常化进程也可能大大加快,反之,若对“零感染”的执念过深,或对风险过度恐惧,也可能延缓这一进程。
全球各国应对疫情的策略与步调不一,进一步模糊了“终点线”,一些国家在奥密克戎波次后已大幅放宽甚至取消所有限制,试图“与病毒共存”;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因国内情况、治理模式或公众预期,采取更为谨慎的渐进式开放策略,这种不同步导致全球疫情此起彼伏,国际旅行与交流的完全恢复仍需时日,只有当主要经济体与人口大国均稳定进入地方性流行阶段,全球层面的“大流行”才算真正告一段落,中国基于国情所采取的“动态清零”政策,在有效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以及何时向下一阶段平稳过渡的复杂考题。
展望前路,新冠疫情的终结更像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冲刺,短期内(未来1-2年),我们或许将看到更多国家根据疫情形势波动性地调整防控措施,社会在开放与谨慎之间寻找动态平衡,中长期看(3-5年或更长),随着更有效的疫苗(如广谱冠状病毒疫苗)、特别是能显著降低感染和传播的鼻喷疫苗等新型疫苗,以及更便捷高效的治疗药物问世,人类应对新冠病毒的工具箱将日益充实,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弥合“免疫鸿沟”,是加速终结疫情的关键。
结论是,新冠疫情没有明确的“终点日”,其消退将是一个渐进的、可能伴有波动的过程,对我们每个个体而言,与其焦虑地等待一个具体日期,不如主动调整心态:接受不确定性,保持科学认知的更新,做好个人防护,积极接种疫苗,疫情的“结束”,最终将体现在我们不再被其主导日常生活,能够以更从容、更智慧的方式与这种病毒长期共存,那一天,并非病毒消失之日,而是我们真正成长起来,学会如何与之共处之时。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