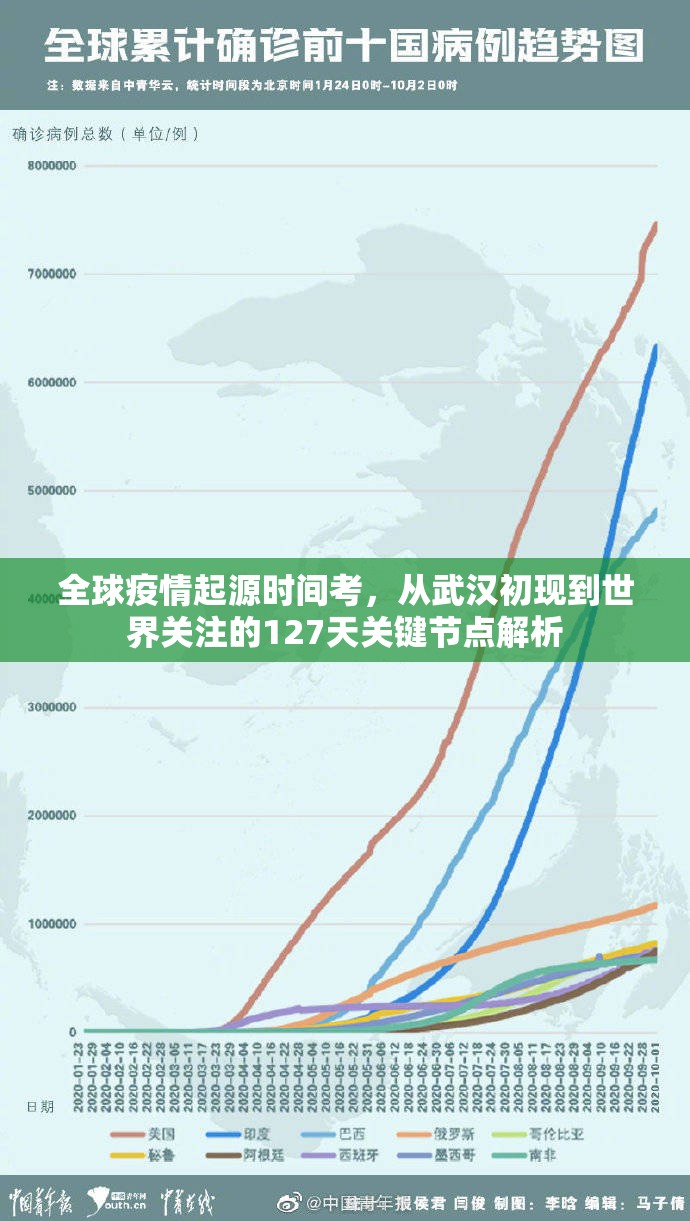“新冠疫情什么时候才结束呢?”

这或许是过去三年多来,全球数十亿人心中反复叩问,却始终未能得到明确答案的问题,从2020年初的恐慌与封锁,到疫苗问世带来的希望,再到变异毒株引发的反复波折,我们仿佛在一条漫长的隧道中摸索前行,远方那象征“结束”的光亮时而清晰,时而模糊,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结束”一词的含义——它并非一个简单的时间点,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科学和心理转变过程。
“结束”的迷思:从“清零”到“共存”的认知转变
在疫情初期,许多人想象中的“结束”,是病毒像SARS病毒一样被彻底消灭,从地球上消失,新冠病毒以其高度的传染性和不断变异的特性,迅速打破了这一幻想,它展现出与人类长期共存的顽强生命力,我们今天探讨的“结束”,不再是病毒的绝迹,而是疫情作为一种全球性紧急状态的终结,以及社会秩序和个体生活回归常态的进程。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23年5月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这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这并非宣告疫情“结束”,而是标志着全球应对疫情的策略从紧急模式转向长期管理模,这好比一场狂风暴雨转为持续的绵绵阴雨,虽然最危急的时刻已经过去,但我们出门仍需带伞。
判断“结束”的多维尺度:科学、社会与心理
我们如何判断疫情在何时“结束”?这需要从三个维度来综合考量:
-
科学维度:病毒的进化与疾病的危害性。 这是最基础的层面,目前的主流科学共识是,新冠病毒将与我们长期共存,其进化趋势是传染性增强、致病性减弱,当新冠病毒变得像普通冠状病毒(如引起部分普通感冒的病毒)或流感病毒一样,其导致的重症率和死亡率稳定在公共卫生系统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我们有有效的疫苗和药物作为常规防控手段时,从科学上讲,它的威胁就已大大降低,奥密克戎及其后续变种虽然传播力极强,但致病力相对减弱,正是沿着这一路径演变,病毒变异仍存在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持续监测。
-
社会维度:公共卫生政策的退出与生活秩序的恢复。 这是最直观的层面,当各国不再要求强制佩戴口罩、取消入境隔离和核酸检测、不再实施大规模封锁和社交距离限制时,我们就会感觉到疫情“结束”了,这个维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个维度,即病毒的威胁是否已降至可接受水平,全球大多数国家已经取消了绝大部分防疫限制,社会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但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审慎、渐进的过程,核心目标是平稳过渡,最大限度地保护生命健康,尤其是脆弱人群。
-
心理维度:集体恐惧的消散与个体心态的平复。 这是最深刻也最滞后的层面,即使科学上病毒已流感化,政策上限制已解除,但疫情留下的心理创伤和行为改变可能需要数年甚至一代人的时间来愈合,许多人仍心有余悸,在拥挤场所会下意识地紧张,习惯性地保持社交距离,对“阳了”感到焦虑,只有当新冠病毒不再主导我们的日常决策和情绪,当谈论它像谈论感冒一样平常时,我们才能在心理上真正宣告疫情的“结束”。
我们正处在“结束”的哪个阶段?
纵观全球,我们正处在从“大流行”向“地方性流行”过渡的阶段尾声,对于中国而言,在经历了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后,随着Omicron毒株特性的变化和全民疫苗接种率的提高,社会面正在有序开放,这是一个关键的“闯关”时期,这个过程必然会伴随阵痛,比如感染人数的短期上升对医疗系统造成的压力。
可以说,在社会维度上,我们正在加速走向“结束”;在科学维度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明确的曙光,但仍需保持警惕;而在心理维度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后疫情时代:我们如何与病毒长期共存?
与其执着于一个具体的“结束日期”,不如将焦点转向如何构建一个更具韧性的“后疫情时代”,这意味着:
- 个人责任的强化: 从依赖强制管控转向主动健康管理,接种疫苗(包括后续的加强针)、在特定场合自觉佩戴口罩、注重个人卫生、提高自身免疫力,将成为公民的日常习惯。
- 医疗系统的加固: 疫情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未来需要持续投资于分级诊疗、重症医疗资源储备和流行病早期预警系统,以应对下一次可能的危机。
- 社会包容与心理重建: 关注疫情对民众心理健康的长远影响,消除对康复者的歧视,构建更包容、更有支持性的社区环境。
“新冠疫情什么时候才结束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行动里,它结束于我们接种疫苗时伸出的手臂,结束于我们理性看待病毒、不再恐慌的心态,结束于社会医疗体系的日益坚固,更结束于我们重新拥抱生活、与不确定性和平共处的勇气。
疫情的“终点线”不是一个等待我们跨越的固定标尺,而是一段我们正在共同走出的漫长隧道,当我们不再频繁地问出这个问题,当我们习惯了下雨带伞、天冷添衣的常态时,那一天,其实就已经悄然而至,我们迎来的,将不是一个与过去完全相同的“昨天”,而是一个学会了与病毒共处、更加珍惜健康与连接的“明天”。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