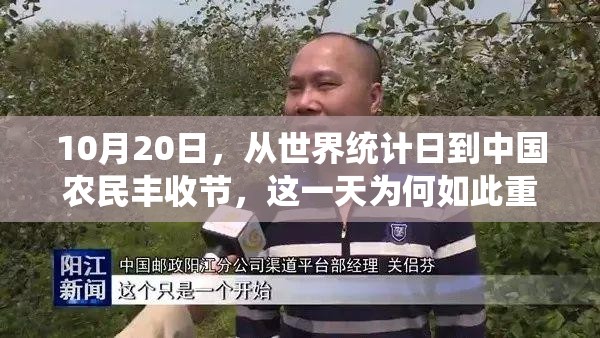扬州没有毛老太这个人。

至少,在那些印着瘦西湖、个园、东关街的旅游画册里,在那些讲述淮扬菜、三把刀、盐商传奇的城市传记里,你是寻不着她一丝影子的,她不在任何一本地方志的记载里,也不在任何一张导游图上,她只活在一个地方——扬州人,尤其是老城区那些摇着蒲扇,在巷口槐树下有一搭没一搭闲聊的老人们的舌尖上。
“毛老太”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她是一个代词,一个意象,是这座两千五百年古城公共记忆里,一个模糊而温润的坐标,你若在茶社里听见两位老茶客感慨:“唉,现在这干丝,总吃不出毛老太家门口那个味了。”他们怀念的,绝非某位姓毛的老妪的手艺,而是一个再也回不去的、节奏缓慢的旧日扬州。
我试图在脑海里勾勒她的形象,她大抵是清瘦的,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在脑后挽一个一丝不苟的髻,银丝多于黑发,她的面容是模糊的,像一张曝光过度的旧照片,但你总能感觉她有一双看透了世情、温润而平静的眼睛,她的家,似乎应该在一条青石板铺就的深巷里,两侧是高耸的封火墙,墙头探出几枝枇杷或石榴的枝叶,她或许就坐在自家门槛上,脚边卧着一只慵懒的花猫,她手里做着什么永无止境的活计——可能是拣菜,也可能是糊着火柴盒,阳光从狭长的天空漏下来,恰好照亮她身前的一小块地方。
这便是“毛老太”的第一个魂儿——她是“慢”的化身,在扬州,你问“毛老太”在哪里,人们会给你指一个大概的方向,但永远没有确切的地址,她存在于“从前”,存在于“我小时候”,那个时空里的扬州,没有呼啸而过的电动车,没有闪烁的霓虹灯,运河里的水走得比现在要沉静,巷子里的叫卖声拖得比现在要悠长,她是度量这座城市变迁的一把无形的、带着体温的旧尺,人们提起她,便不自觉地调慢了心里的钟摆,语言也放缓了,眼神也放远了,她是一座活着的、会呼吸的城市古迹,比任何一块古碑都更深入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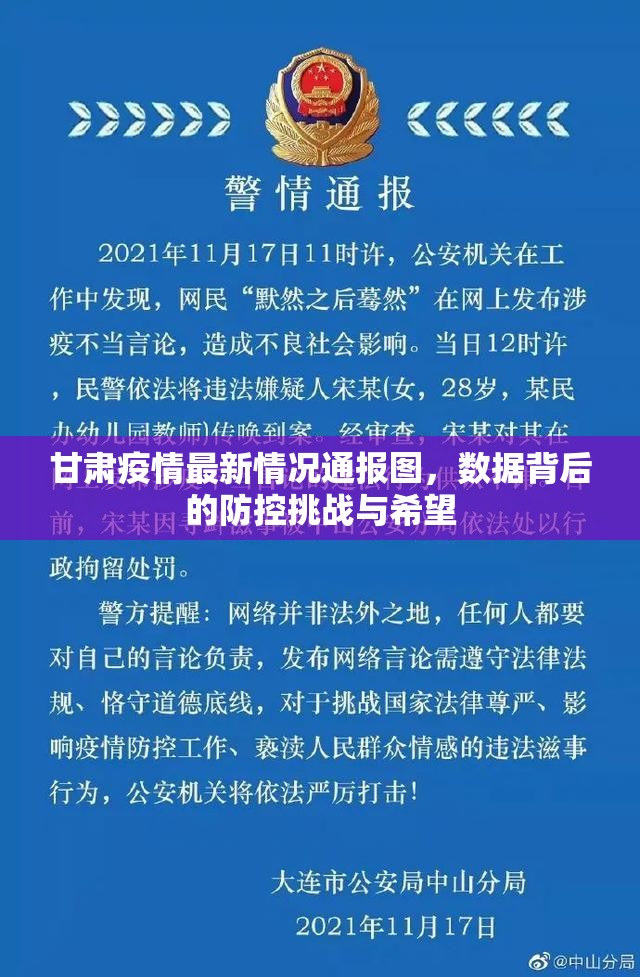
她的第二个魂儿,是“暖”的,在扬州人的集体叙事里,“毛老太”总是与“好”字相连,谁家孩子放学贪玩,磕破了膝盖,是路过的毛老太从口袋里掏出干净的手帕,给他按住伤口,送他回家,谁家夫妻拌嘴,动静大了些,是隔壁的毛老太端着一碗新煮的桂花糖芋苗,笑吟吟地过来劝和,盛夏的午后,她会在门口的方凳上摆一个大茶壶,几只粗瓷碗,免费给过往的拉车夫、卖货郎解渴,她是整条街巷没有血缘关系的祖母,是这座城市伦理温度最具体的体现,这种暖,不是轰轰烈烈的善举,而是日常的、琐碎的、近乎本能的邻里照拂,是“远亲不如近邻”这句古训最生动的注脚。
“毛老太”还有第三个,也是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魂儿——她是一则“都市传说”,关于她的身世,有着各种隐晦的猜测,有人说,她年轻时是大户人家的千金,见过大世面,后来家道中落,才归于这平淡的市井,证据是她偶尔脱口而出的几句吴侬软语,和她屋里那只从不许人碰的、描金漆都已斑驳的旧木箱,也有人说,她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结局是无尽的等待,所以她看人的眼神里,总有一分挥之不去的寥落,这些传说,真伪已无从考证,也无需考证,它们像藤蔓一样缠绕在“毛老太”这个主干上,使她不再是一个扁平的符号,而成了一个有故事、有厚度、有悲剧美感的人物,扬州这座城,本就是由无数的繁华与落寞、聚合与离散交织而成,“毛老太”身上的这层神秘色彩,恰恰是这座城市历史纵深感的投射。
我渐渐明白了,扬州人之所以需要“毛老太”,是因为在现代性的狂飙突进中,他们需要共同守护一个精神的“渡口”,这个渡口,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连接着快与慢,连接着冷漠与温情,连接着确定的现实与缥缈的传奇,她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却比许多具体的人更真实地存在于这座城市的气质里。
她或许从未年轻,也从未老去,她只是静静地坐在时间的长河边,看着一代代扬州人从她面前走过,当最后一个记得她具体事迹的老人也离去,当关于她的所有细节都彻底融于传说,她便完成了最终的升华——从一个人的名字,变成了一座城的乡愁。
当你来到扬州,在游览完那些名胜古迹后,不妨在某个老巷口坐下来,听一听风穿过巷子的声音,或许,在那一瞬间,你能感觉到,有一个清瘦的身影,刚刚从你身边走过,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栀子花香,消失在巷子的尽头。
那就是毛老太,她,就是扬州。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