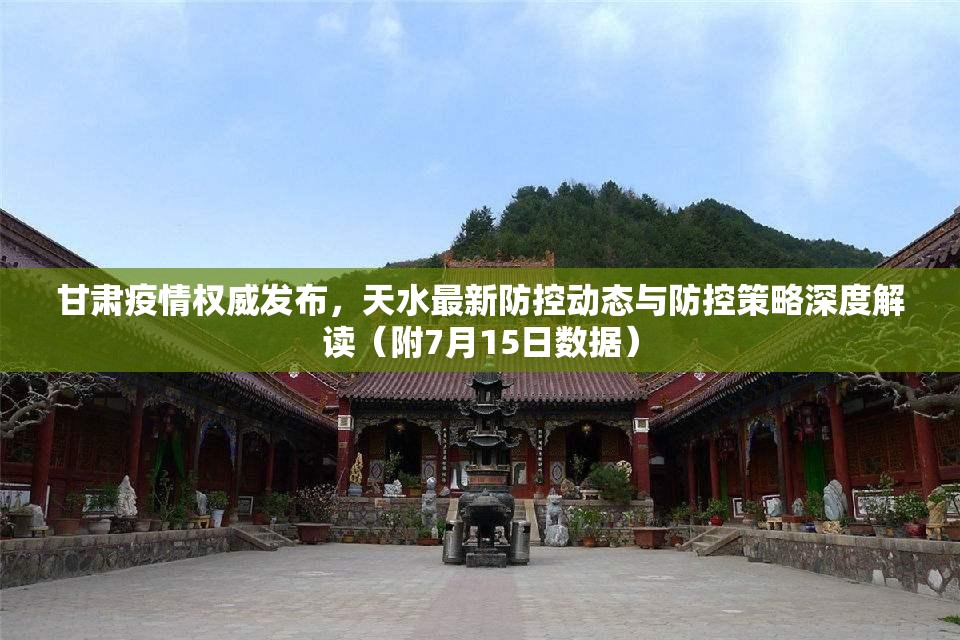“疫情什么时候放寒假啊?”

这句话,或许曾无数次在你我的心头盘桓,或是在与亲友的闲聊中不经意地滑出唇边,它不像一个严谨的科学问题,更像是一声疲惫的叹息,一种对“正常”生活的深切渴望,这短短十个字,承载了三年多来全球民众共同的情感重量,它叩问的,早已不仅仅是病毒本身的消长规律,更是我们个体与集体在巨大不确定性中,对秩序、安宁与心灵假期的深切呼唤。
“疫情”与“寒假”:一个错位的隐喻
从字面上看,“疫情放寒假”是一个有趣的修辞搭配。“寒假”,是校园生活中一个规律性的、被承诺的休憩节点,它意味着一段紧张学习后的放松,是时间轴上明确无误的驿站,而“疫情”,自2020年暴发以来,其发展轨迹却充满了不可预测性,它不像一个有固定课程表的学期,我们无法预知它的“期末考试”在何时,更遑论一个清晰的“假期”。
当人们发出“疫情什么时候放寒假”的疑问时,实际上是在用一种熟悉的、周期性的时间概念,去丈量一种陌生的、非线性的混沌体验,这是一种试图将不确定性重新纳入可控认知框架的努力,我们渴望给这场漫长的全民“大考”划上一个休止符,期盼能像期待寒假一样,在某个确定的日期,暂时或永久地卸下口罩、行程码、核酸报告与社交距离这些沉重的“课业负担”,回归到那个可以自由呼吸、肆意拥抱、畅快旅行的“假期”生活。
疫情的“学期”: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漫长课业?
回顾过去几年,疫情的“学期”无疑是一堂沉重而深刻的全民课程。
第一学年,是“恐慌与适应”,我们学习了如何佩戴口罩、如何正确消毒、什么是社交距离,网课、远程办公从新鲜事物变成了常态。“ lockdown ”(封锁)成为了年度词汇,这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我们被困在方寸之间,重新审视着与外界、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
第二学年,是“焦灼与反复”,疫苗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病毒的变异(如Delta、Omicron)又让局势一波三折。“清零”与“共存”的争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我们的生活像是在开合不定的拉链中穿梭,时而放松,时而收紧,疲惫感与迷茫感开始滋生,“何时是个头”的疑问越来越强烈。
第三学年及以后,是“调整与共存”,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和病毒毒力的演变,许多国家和地区逐步调整了防疫策略,尝试着与病毒共存,中国也因时因势优化防控措施,走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病毒的传播并未彻底消失,它从一场席卷一切的“海啸”,变成了不时泛起的“波涛”,我们学会了在病毒的背景下生活,但内心深处,对那个可以完全无视其存在的“寒假”的期盼,从未熄灭。
“放寒假”的深层意涵:我们究竟在期盼什么?
当我们追问“疫情什么时候放寒假”,我们期盼的究竟是什么?
是对确定性的渴望,疫情打乱了所有既定的计划,旅行、聚会、甚至简单的回家探亲都变得困难重重,我们期盼一个明确的终点,一个可以安心做长远规划的时间点,让生活重新回到有章可循的轨道上。
是对身心自由的回归,长期的防疫措施,尽管必要,但也无形中构筑了物理与心理的藩篱,我们期盼能毫无负担地摘下口罩,看清彼此的笑容;能随心所欲地去往远方,感受异域的风情;能与亲友紧密团聚,无需担忧潜在的风险,这是一种对完整社交生活和行动自由的深切呼唤。
是对心灵疲惫的疗愈,持续的焦虑、对健康的担忧、隔离带来的孤独感、经济压力……这场疫情给全球民众的心理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期盼的“寒假”,是一个能让集体心灵得以喘息和疗愈的时期,是压力释放、情绪修复、重拾生活热情的过程。
展望:没有“寒假”的终点,只有不断前行的我们
像季节性流感那样有明确“寒假”(即低流行期)的疫情阶段,对于新冠病毒而言可能难以精确预测和实现,它更可能成为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呼吸道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也已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志着全球抗疫进入新阶段。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期盼落空,随着科学认知的深入、医疗资源的储备和防护意识的普及,我们正在学习如何与病毒共处,如何将疫情的影响降至最低,那个绝对的、一劳永逸的“寒假”或许不会以我们想象的形式到来,但通过社会与个体的共同努力,我们正一步步地将“疫情生活”重新定义为“正常生活”。
“疫情什么时候放寒假啊?”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它作为一句时代性的叩问,真实地记录了我们这段共同经历的迷茫、坚韧与期盼,它提醒我们,健康与平凡的可贵,自由与相聚的值得,也许,最终的“寒假”并不存在于某个外部的宣告,而是内化于我们每一次勇敢的面对、每一次科学的防护、每一次对生活的热爱之中,当我们能够坦然面对病毒的存在,同时又不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创造时,我们心灵的“寒假”,便已悄然开始。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