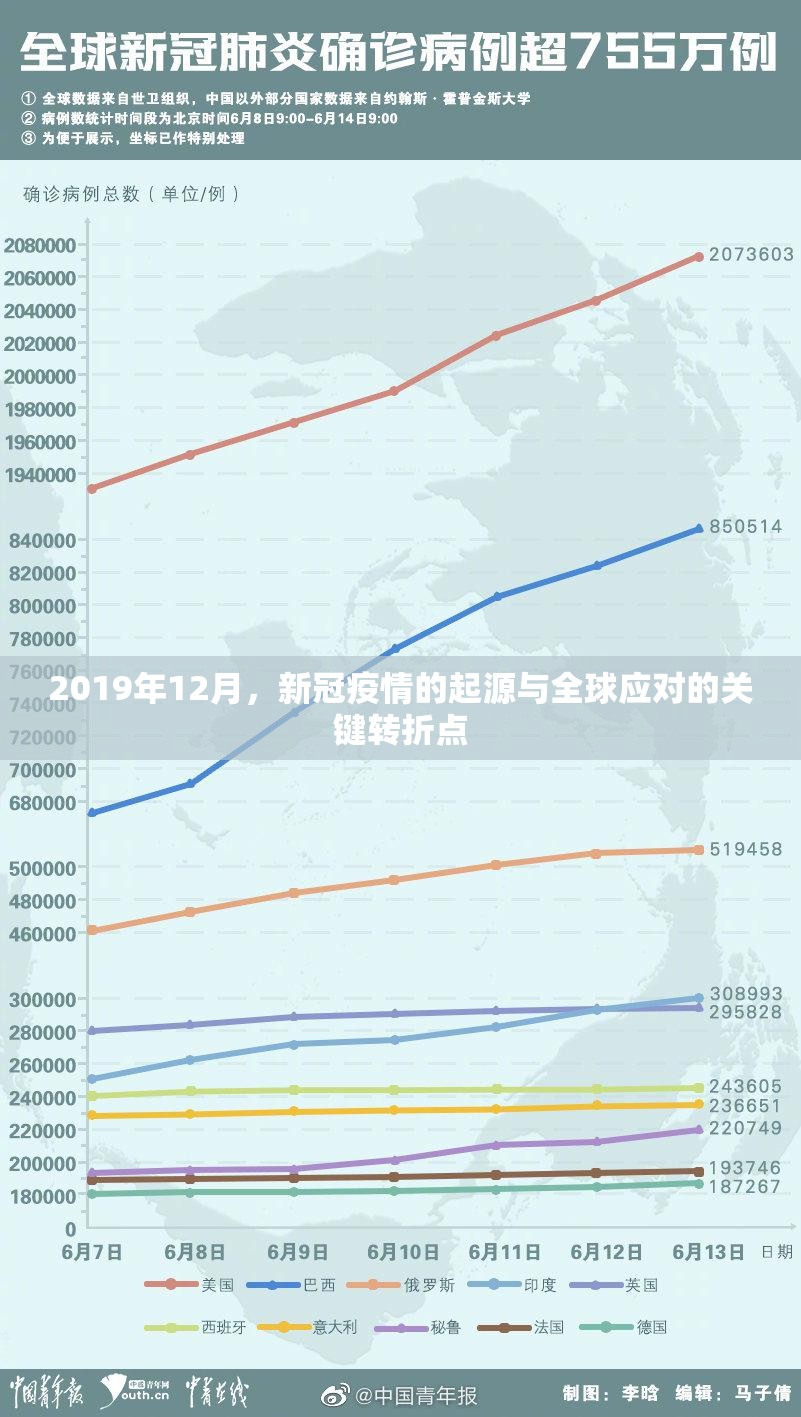当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3月11日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时,很少有人能预料到这场卫生危机会持续如此之久,更少有人能想象它将对全球社会结构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三年多过去了,“新冠疫情何时能结束”这一问题依然萦绕在每个人心头,而答案却比我们最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从流行病学视角看,疫情“结束”并非一个瞬间事件,而是一个渐进过程,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并非某天突然终止,而是病毒在经过几波感染后逐渐减弱为季节性流感,新冠疫情很可能遵循相似路径——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出现标志着病毒进化进入新阶段,其高传染性、相对较低致病性的特点暗示病毒正朝着与人类共存的方向演化,全球通过自然感染和疫苗接种建立的免疫屏障正在形成,但病毒变异的不可预测性意味着我们仍需保持警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多次强调,“疫情结束的条件取决于全球疫苗接种覆盖率、有效的治疗方法以及持续的国际合作”。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重塑作用已经显现,远程办公从临时措施变为常态,数字经济发展加速,全球供应链重新布局,这些变化不会随着病毒消失而逆转,而是成为后疫情时代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产出累计损失超过12万亿美元,这种创伤需要多年才能修复,更深远的是,疫情暴露了全球化的脆弱性——边境关闭、贸易中断让我们意识到高度互联的世界也存在致命弱点,未来世界可能会寻求一种“有韧性的全球化”,在享受互联互通好处的同时,建立更好的风险防控机制。
社会心理层面的“疫情结束”可能比生物学上的终结更为滞后,焦虑、抑郁和社会疏离感在许多人群中持续存在,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全球焦虑和抑郁患病率在疫情第一年增加了25%,这种心理创伤将影响一代人,人们对密集场所的谨慎、对个人卫生的重视、对远程互件的依赖,这些行为模式可能长期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结束”,需要社会集体心理从危机模式转向常态模式,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共同努力。
国家间合作与竞争关系的重构是疫情另一重要遗产,疫苗民族主义、医疗物资争夺战暴露了国际治理体系的缺陷,但同时也催生了诸如“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等多边合作机制,疫情提醒我们,病毒无视国界,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未来全球卫生治理需要更强大的国际合作机制,这不仅是应对当前疫情的需要,也是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危机做准备。
展望未来,新冠疫情或许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束日期”,而是逐渐转变为地方性流行,成为人类传染病谱系中的一部分,类似于季节性流感,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何时结束”的思维转向“如何共存”的思维,各国正在制定的“与病毒共存”策略正是这种范式转移的体现——通过持续监测、疫苗接种、医疗系统强化和社会行为调整,将疫情影响降至最低。
疫情终将退去,但它留下的教训和改变将持久存在,它迫使人类重新思考公共卫生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地位,重新评估全球合作的价值,重新认识社会脆弱群体的重要性,也许疫情真正的“结束”,不在于最后一个病例的消失,而在于我们能否从这场全球危机中学习、成长,构建一个更具韧性和公平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新冠疫情何时能结束世界?答案可能是:它永远不会完全结束,但它将催生一个新世界——一个更加数字化、更注重健康、更意识到互联互通的双重性,也可能更加珍惜面对面人类接触的世界。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